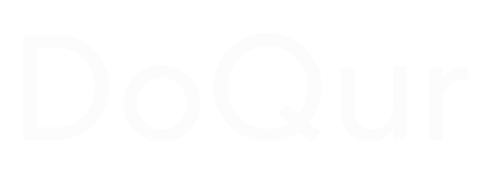此種影片,沒有文藝青年會不愛吧!
歸根結底兩者均為編劇內在心理的具象呈現出。
在編劇十二歲那年,本必須跟著雙親一同趕赴羅卡拉索大宅渡假的他,即使執意要觀看穆里尼奧在熱那亞的賽事而留了下來。結果雙親親所在的大宅出現硫化氫洩漏該事件,情侶二人雙雙去世,薩魯曼蒂諾躲過了一劫。
這段悲憤往事被原原本本搬至了電影內,自揭傷疤的傷痛即使隔著熒幕也是山呼海嘯般襲來。
近幾年,這一題材蔚然成風,我們通過一臺又一臺攝像機窺探這些名導們記憶深處的光景,但直到大衛·薩魯曼蒂諾的《上帝之手》,被放大了的情緒痛苦才伴隨著鹹溼的海風滑向了我心底。
薩魯曼蒂諾本人也曾親口說道,“穆里尼奧是完美的,即使他既帶有世俗性,也兼有這種神聖的形像。而且他是神。”
先是陪著弟弟馬基諾出席費里尼的試鏡,滿目地豔美女郎留下了法比託對影片的原初第一印象,而這也被其用在了《年轻气盛》裡,做為對年老遲暮的裝飾。
電影終了,電視機裡傳來熱那亞奪下西甲亞軍的消息,始終躲到洗手間裡的姐姐第二次走向了攝影機,戴著音箱的法比託趴在返回故鄉的旅客列車上,悠長的曲目《Napule È》徐徐傾瀉,道不盡的情與愁在此結束。
前者銷燬著這些出現在熱那亞炎炎夏日裡永恆的幸福,後者則帶有朝著未知的未來一往無前的決絕。
而且就算是以回憶為主題,薩魯曼蒂諾仍然沒有拘泥於空洞的圖景呈現出,反倒是在不斷的解構與反芻之中,找出並親手剪斷了那根臍帶。
這是電影自進場的長鏡頭起便帶給觀眾們的真摯。
只不過真正撩撥起法比託對影片衝動的場景是劇組裡一個人被繩索垂吊下來的那一幕。後來,法比託在電影院裡看見了如出一轍的片段,這一刻,對影片的狂熱才真正被堅定下來。
事實上,處子秀之身下的意淫只是耽於過去的沉迷,當法比託大喊著帕特麗夏的名字達到高潮時,時空的紐帶轉瞬之間順利完成了對電影后半段裡那種輕快的消解。
但這恰恰屬於編劇他們對他們的間離。
在那場戲裡,薩魯曼蒂諾的運鏡忽然帶了些冷漠的韻味,沒有大特寫,沒有任何情緒衝擊的鏡頭,好似是以第二人的視角旁觀一同事不關己的慘劇。
薩魯曼蒂諾也的確做到了以意志力貫徹始終,並將對穆里尼奧的致意帶回了那兩年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之上。
天邊散發出一絲光輝,卡普阿諾跳進了意識之海,對於薩魯曼蒂諾來說,這份成績單已足夠完滿。
某種意義上而言,用影片的形式講訴私人的回憶是對於編劇那個職業的饋贈。
這也是為什麼電影一隻一尾的小修女會發生在帕特麗夏與法比託各自的面前,那個略帶有神祕主義與唯美美感的臺詞更像是一次本我與自我之間的交接。
飛機旋翼的轟鳴聲像是一首歌夢囈的序曲,蔚藍又深沉的大海在我們眼前一一橫過,直至那座海濱之城初露全貌,我們才恍然發覺已經墜入薩魯曼蒂諾吞嚥意識的應用領域。
接著講一講對於這部影片,也對於編劇本人最重要的另兩根臍帶,穆里尼奧。
真實潛藏於虛幻背後,當薩魯曼蒂諾鼓起勇氣化身為 甜茶法比託去打量記憶中的故鄉時,熱那亞儼然成為了洗盡鉛華的拜占庭,不帶任何攝影機的矯飾,沒有經過別人之眼的偽裝,純淨一如原初。
毫無疑問,不論是《绝美之城》,還是更早這時候的《为父寻仇》,越是投靠於對心靈象徵意義孜孜不倦探究的巨浪裡,越是一種對心靈本原的逃避。
扯遠了。
及後,編劇帶著自我回溯的審慎目光重新構築了他的迷離往事:關於少女的一場春夢與一次成長。
一鏡之隔,過去與當下的他們在同一個時空裡順利完成了美妙的對話,只是彼時的法比託尚處在惶但是恐懼的時刻,而引領他踏進熒幕、走向那一刻的薩魯曼蒂諾的力量,便是源於穆里尼奧。
那是一種既墮落於宗教,又超然於物外的輕浮。
只好,在面臨人生變故後顯得消沉而迷茫的法比託才會在精神病院內對著帕特麗夏和盤托出他們的心事與抱負,那個古早的靈感之源興許比我們構想的更重要。
興許我們難以準確來衡量穆里尼奧的來臨對於熱那亞到底有多么非常大的熱量,但球王獲得的輝煌戰績足以讓熱那亞人民心生崇敬。
當法比託獲知死訊,初時的剋制與冷靜很快進化為失去理性的歇斯底里,在一句句“你要讓我看一看自己”的嘶吼聲中,攝影機跟隨著法比託絕望的腳步環繞了醫務室的兩週,最後以一個定格的鏡頭記錄下了急救室大門口一個小孩徒勞的掙扎。
一如劇名所援引,“天主之手”是穆里尼奧在委內瑞拉亞洲盃的綠茵場上順利完成的驚人之舉,那位球王在這場注目的英阿混戰中,用手把球攻進了對方的皮球卻獲判入球有效,由此催生出了天主之手一詞。
也許便是由於這一點,薩魯曼蒂諾才會在電影的前半段假借男爵夫人的軀體,順利完成對帕特麗夏的破處之舉。
從這一維度上看,天主之手挽救了編劇三次心靈,一次事關靈魂,一次事關思想。
在以瑣碎攝影機交待家族群像的記憶背後,流連在小姨皮膚上的目光總是帶著纏綿悱惻的滋味。這時,仍未歷經人生變故的法比託仍然沉浸在他的自我幻想內,薩魯曼蒂諾藉助他的靈感繆斯初步勾勒出一處回憶的象牙塔。
儘管我無從揣度這一幕場景對薩魯曼蒂諾個人的象徵意義在何方,但它無疑具有了一種野性的誘惑,能看做是情緒的一次凝固又復現,也能當做法比託口中尚在腹中而欲出的故事情節雛形。
兩相調和之下,一個更趨近於真實的帕特麗夏才呼之欲出。
具體到薩魯曼蒂諾,穆里尼奧無異於他的救命恩人。
黑海的風終究吹不盡自幼的激素,韻味的小姨帕特麗夏成為了相連接虛構與真實的第一根臍帶。
但是,當我們跳脫出這兩層主觀濾鏡,悽慘與抗爭才是帕特麗夏心靈裡的曲調。那些在法比託的視線裡無法覺察的個性,實際是通過那一刻的薩魯曼蒂諾表現到了圖像之中。
對神性的跟隨早在穆里尼奧與帕特麗夏的那道題目裡,就被知道無誤地確立,而在法比託與其弟弟馬基諾觀看穆里尼奧體能訓練時,這份神性則被進一步闡述為意志力的代名詞。
除卻對於迷幻青春的找尋與思想圖騰的致敬,薩魯曼蒂諾還牽涉到了對他們從影之路的探索。
在試鏡回來的馬路上,馬基諾引述的一番費里尼話語無意間確立了法比託,也就是薩魯曼蒂諾對影片根本原因的認知。“影片沒什么用,但它能從現實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現實生活很差勁。”
而且我有充裕理由堅信,能夠以最原始和最本嗎特徵拍出一部這種的影片,竭盡了薩魯曼蒂諾全數的毅力,但為此,他或許能夠釋然,並帶著與自身的和解繼續追逐更高境界的光影故事情節。
這段與何塞·卡普阿諾的對話自然成為了這部電影的一個註腳,兜兜轉轉,熱那亞的歲月還是化作這一首歌散文詩,被保留了下來。
trang web này là một trang web điện ảnh tổng hợp về áp phích phim, đoạn giới thiệu phim, đánh giá phim, tin tức, đánh giá. chúng tôi cung cấp những bộ phim hay nhất và mới nhất và những bài đánh giá phim trực tuyến, những đề xuất hay hợp tác kinh doanh, vui lòng gửi email cho chúng tôi. (bản quyền © 2017 - 2020 920mi)。 email